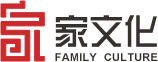文章转自先秦秦汉史 周振鹤

周振鹤,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,代表作《西汉政区地理》。
备注:
象郡是秦朝的郡级行政区,辖今广西西部、越南中北部,初设于公元前214年,是秦始皇在岭南地区设置的三郡之一(另两郡是桂林郡和南海郡)。
赵佗(约公元前240年—公元前137年),恒山郡真定县(今中国河北正定县)人,原为秦朝将领,与任嚣南下攻打百越。秦末大乱时,赵佗割据岭南,建立南越国。
南越国,又称为南粤国,在越南又称为赵朝,是约公元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,国都位于番禺(今广东省广州市),全盛时疆域包括今天中国广东、广西的大部分地区,福建的一小部分地区,海南、香港、澳门和越南北部、中部的大部分地区。
日南郡是中国古代上一个郡的名字,其范围在今天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部地区,辖境位于越南横山以南,即从广平省到平定省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带。汉武帝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,西汉王朝灭南越国,在百越地区设置了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珠崖、儋耳共9个郡,隶属交趾刺史部。
秦汉象郡新考
秦始皇三十三年取五岭以南陆梁地置为南海、桂林、象郡。秦亡以后,南海尉赵佗拥三郡自立南越国。汉兴,无力用兵岭南,赵氏政权延续近百年之久。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,置十郡,比秦代疆域有所扩大。昭、元两代相继罢省儋耳、象郡、珠崖三郡,此后至西汉末年,岭南地区并存有南海、苍梧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七郡。
在从秦代三郡到汉末七郡的转化过程中,最成症结的问题便是象郡的沿革。由于对史料取舍的不同,历来的中外学者对象郡的去向基本上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:一则以为象郡自秦延续到汉昭帝元凤五年间,其领域大致跨《汉书.地理志》郁林、牂柯两郡间;一则认为秦象郡相当汉日南郡,秦亡后即已消失。本文试图对这两种观点的立论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,以求得出象郡沿革的正确答案,就正于对这一问题有所研究的同志。
一、两种对立的观点:日南说和郁林说
清代以前,未有学者对象郡的变迁作过全面的论述,一般只是接受《汉志》日南郡下班固自注“故秦象郡,武帝元鼎六年开,更名”的说法,模糊地认为秦象郡应相当于汉日南郡。至于象郡范围到底多大,如何转化成日南郡,始终没有过详细的考订。杜佑《通典》虽然认为秦象郡范围应包括汉日南、九真、交趾三郡全部及郁林、合浦两郡部分地,但亦不详其原因。杜说一直为唐以后的学者所尊奉,杨守敬的《嬴秦郡县图》即据之以作。
一九一六年,法国人马伯乐(Henri Maspero)对象郡问题提出了新看法,他依据下列史料:
1、《山海经.海内东经》篇末〈沅水〉条云:“沅水出象郡镡城西,东注江,入下隽西,合洞庭中。”〈郁水〉条曰:“郁水出象郡,而西南注南海,入须陵东南。”
2、臣瓒注《汉书.高帝纪》引《茂陵书》曰:“象郡治临尘,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。”
3、《汉书.昭帝纪》载:“元凤五年......罢象郡,分属郁林、牂柯。”
得出象郡地跨《汉志》郁林、牂柯两郡间,自秦延续至汉昭帝时方才罢省的结论。此说可简称之为“郁林说”。
七年后,另一法国人鄂卢梭(L. Aurousseau)著文指责上述史料不可依据:
1、《山海经》“ 奇异而迷离不明”,其材料不应采用。
2、《茂陵书》所述有脱误。临尘乃临邑(即林邑)之论,依里距看,象郡治所应南至汉日南郡之象林(即林邑)。
3、《汉书.昭帝纪》此载“毫无根据”,必须毅然摒除。
同时,鄂氏辑录了七类三十四条史料,据之维护秦象郡即汉日南郡的旧说(可简称其为“日南说”),明确指出,秦亡以后,象郡既废,不得再存在象郡问题。
马、鄂之争在学术界颇具代表性。六十年来,有关象郡的论文,基本上不归马即归鄂,见仁见智,相持不下。不同的结论乃来自不同的依据,因此必须对马、鄂两氏所用史料进行认真分析,详加甄别,才能决定取舍,有所依违,对象郡问题作出正确判断。
二、日南说所据史料可疑
鄂文的份量较大,其中对马氏的批评留待后文讨论,这里首先对其所列举的大量史料作一分析,以确定其是否可据。鄂氏所引用的史料虽然洋洋洒洒,但细读之下,能作为其结论的坚实依据的实仅数条而已。其余有的只是“凑数”(鄂著的中译者冯承钧语),如第七类的安南载籍;有的亦不直接证明象郡日南说,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许多引文;有的其实要帮他的倒忙,如《淮南子》、《交州外域记》、《广州记》等。
最能支持日南说的史料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条:
1、《汉书.地理志》日南郡本注:“故秦象郡,武帝元鼎六年开,更名。”
2、《史记.秦始皇本纪》集解引韦昭注象郡曰:“今日南。”
3、《水经.温水注》引王隐《晋书.地道记》曰:“(日南)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,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。”
4、《温水注》:“浦口有秦时象郡,墟域犹存。”
这些史料表面上看来出自不同载籍而殊途同归,证成了象郡日南说。但仔细作一透视,四条史料实则同出一源,都本于《汉志》的注文。
班固《汉书》成于东汉中期,其后即广为流传。韦昭是三国吴人,作过太史令,参与《吴书》的撰述,并著有《汉书音义》七卷,因此他注《始皇纪》乃因《汉志》之注文,并非别有所据。看他注桂林郡曰:“今郁林也”,也是本《汉志》郁林郡班注:“故秦桂林郡”而来,便知其中原委。因此,韦昭注实在不能充作一条证据。
王隐是晋人,其《地道记》成书于东晋时,上距秦代已五百来年。象林县是汉日南郡最南端的县,但在《地道记》以前没有任何载籍提到过秦象郡亦有名为象林的属县。无论《史记》或《汉书》对象郡的叙述都很模糊,甚至连其方位、郡治都未正面提及,更不用提其属县了。但秦亡几个世纪以后才出现的《地道记》竟明确指出秦象郡属有象林县,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。清人钱大昕论运用史料的原则时曾说:“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,非古人之不足信也,古人之前尚有古人,前之古人无此言,而后之古人言之,我从其前者而已矣。”有一定道理。故王说未可轻信。推其“秦象郡象林县”之由来,无非因郡名与县名近似而发生的联想罢了。遂以为后者也必辖有该县了。《地道记》中的无端臆想并不止这一条,还有如“交趾郡赢阝娄,南越侯织在此”的毫无根据的记载。南武侯织(王隐误武为越)高帝时封为南海王,其封地虽不能确指,要在汉初庐江郡与闽越、南越交界处殆无异义。《史》、《汉》明言织为闽越王无诸一族,又言南海王织上书献壁皇帝,淮南中尉擅燔其书,不以闻,复言南海民处庐江界中反,淮南吏卒击之,以此知南海地必在淮南国庐江郡南部边界。若交趾赢阝娄地远在赵佗南越国之后方,如何与庐江郡发生关系?《地道记》此文之虚妄,显而易见。因此《地道记》这一不可靠记录并不能作为日南象郡说的证据,相反却应看作是对日南即象郡这一说法的演绎。
又过了二百年,到北魏郦道元写《水经注》时更进一步断定:“浦口有秦时象郡,墟域犹存。”但《温水注》这一条注文十分突兀,在其前不云有浦,办只云郎湖,在其后犹接叙该湖,故“浦口”之浦,不知指何浦,王先谦以为指郎湖浦口,似不通,但该注文确插入郎湖事中;鄂卢梭氏以为指卢容浦,但前后注文一并具引如下:“颇疑此文自城南,东与卢容水合,东注郎究,究水所积下潭为湖,谓之郎湖。浦口有秦时象郡,墟域犹存。自湖南望,外通寿泠,从郎湖入四会浦。......自四会南入,得卢容浦口,晋太康三年,省日南郡属国都尉,以其后统卢容县置日南郡及象林县之故治。《晋书.地道记》曰:“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。”从这一段文字看来,实在很难判断象郡墟域到底犹存于那个浦口。鄂氏认定其为卢容浦口,自有深意。因《温水注》说汉日南郡治为西捲县,而该县也正位于卢容浦口,鄂氏因此说:“秦象郡同汉日南郡的前后治所,既在同一地方,此事若实,前《汉书》或者因此说汉日南郡即是故秦象郡。”但是以这样的方法来论证秦象郡与汉日南郡同在一地是很危险的。因为:(一)象郡墟域究地何处,尚需认真推敲;(二)西汉日南郡是否治西卷尚待证明,《温水注》引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曰:“日南郡,治西捲县”,乃是东汉之制,有人以为西汉日南郡应治《汉志》该郡之首县朱吾;(三)《水经注》一书凡提及秦郡治所时,必详其治于何县,“象郡墟域”一语甚为含糊,似乎即指象郡治之墟域,然则此象郡治是什么县?既其名无考,在秦亡六百年之后又有何根据,判断其必为象郡治?令人无从信服。
考证地名和政区沿革本非道元所长,如西汉侯国至班固时多已不能指两地,但《水经注》往往一一指明,结果造成笑话。或一侯国分指两地,或应在甲地而附会为乙地。甚至《汉书》已指明其地的《水经注》依然自编自唱。如成安侯韩延年国,《汝水注》以为在颍川之成安,《泒水注》又作陈留之成安,实际上《汉表》明载其国分自郏县,应在颍川。临羌,《河水注》以为孙都之侯国,不知武帝封孙都时,临羌地尚未属汉,且孙都之封实在临蔡,并《汉书》亦未细读。《浊漳水注》以信都辟阳亭为审食其侯国,但本传言辟阳近淄川,非信都之辟阳明甚。此类例子比比皆是,悉出于顾名思义、因缘附会,想当然耳。颇疑《温水注》所谓象郡墟域亦是受《汉志》日南即象郡说法的影响而误认,此墟域非郦氏亲历至为明显,大约亦得之某种传闻,而以论传论。因此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,不便贸然相信这一墟域必定是秦之象郡治。
有此三端,而欲证明秦象郡与汉日南郡治同在一地,不亦难乎?大约有鉴于此,所以鄂氏乃以“此事若实......”的两可语气代替绝对的肯定。
《温水注》还有一段文字,鄂氏以为能引作强证的,其实还不如前所归纳的几条过硬。这里亦一并作一分析:“浦西,即林邑都也,治典冲,去海岸四十里,处荒流之徼表,国越棠之疆南,秦汉象郡之象林县也。东滨沧海,西际徐狼,南接扶南,北连九德,后去象林林邑之号,建国起自汉末,初平之乱,人怀异心,象林功曹姓区,有子名连,攻其县杀令,自号为王,值世乱离,林邑遂立......。”
鄂氏以为此文“明说古占波最初都城象林,就是秦汉象郡之象林县,又可证明汉日南郡同秦象郡的南境是在同一地方”。这个证明真是糊涂。按鄂氏之观点,秦象郡即汉日南郡,亦即秦有象郡而汉无象郡,则注文中“秦汉象郡”一句本身就大不通。汉有象林县,但秦有否象林县尚待证明,怎能以此未经证明的说法去证明汉日南与秦象郡的南境同在一地?所谓秦象郡有象林县的说法与前述《地道记》同出一辙,无庸多议,“秦汉象郡象林县”的提法说明了郦道元对秦象郡与汉日南郡关系的认识模糊。
退一步讲,如果我们承认秦有象林县,那么,鄂氏到底以那一个象林县为准?以《温水注》本文,还是以《地道记》?前者相当《汉志》日南郡象林县,后者则相当同郡之卢容县,两者相去数百里之遥。西汉日现郡之象林县即后来之林邑国都,东汉永和二年(《温水注》以为初平间)“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,烧城寺,杀长吏”。自此以后,象林县即不复归于中国版图。晋代曾一度复置象林县,但只是侨置于卢容县而已,已非西汉象林故地。《地道记》所谓“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,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”,就是以晋之日南郡治卢容县(亦是侨置之象林县所在,汉卢容县同此)当秦象郡象林县地。而郦道元之“秦汉象郡象林县”,则在晋象林县以南数百里。两个所谓“秦象林县”的差异体现了后人对象郡日南说的看法十分今糊,这种模糊认识发展到清代阎若璩就干脆说秦象郡治象林县,而不需要任何证明。鄂氏亦无视两个象从的差异说明秦郡象林县在他心目中也并不清楚,以此何能证成象郡日南说。
综上所述,能够支持鄂氏观点的最过硬史料无非就只《汉志》本注一条。其他几条不过是后人因此注文而作的推论和演绎而已。但是《汉志》本注也并不见得都是绝对可靠的,尤其在郡国沿革方面有许多靠不住的地方。如所谓“高帝置”之郡,竟有三分之一以上实非高帝时所置;记述河西四郡之置年,则无一是处;广陵厉王之封域不足广陵一郡,而误以为兼有鄣郡之地;六安国乃以九江郡地置,却错当成是衡山国后身。凡此种种,说明班固不太精于地理沿革,许多注文出于想当然,因此不能过于迷信。
一般地说,《汉志》本如果发生错误,就是在发现矛盾以后通过《史》、《汉》有关纪传表志的综合考证纠正的。现在关于日南郡即“故秦象郡”的注文明显与《昭纪》“罢象郡,分属郁林、牂柯”的记载发生冲突,因此这条注文是否可靠就值得慎重斟酌了。一般而言,本纪往往比地志注文可信,这是一;《昭纪》此载又有时代相去不远的《海内东经》和《茂陵书》作旁证(详后),而《地志》注文却仅是一条孤证,这是二;第三,这是最重要的:如果以日南说能圆满解释象郡的沿革而不与其他史料相牴牾,则日南即象郡之注文亦未可全非,然而遗憾的是,鄂氏持此说去设想岭南地区的沿革,虽然随意曲解史料而且加上许多臆想笔假设,仍然得不到满意的解释。相反,如果根据《昭纪》所载(即郁林说)来看象郡变化,则圆通无碍,因此《地志》的注文实际上是不可信的。在举例说明日南说之不通与郁林说之可行以前,必须先分析鄂氏对马氏所引史料之责难是否真有道理。
三、郁林说所据史料可信
先说《山海经》。鄂氏对此书的地理内容全面否定态度。《山海经》当然是一部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语怪之书,但其中所包含的地理资料反映了作者在创作该书的地理知识,这是今天人所共的事实。而且具体就《山海经》各篇内容而言,存在一定的差异,如《五藏山经》部分就比较平实雅正,包含丰富的地理内容。至若马伯乐氏所举沅水、郁水两条文字,更与《山海经》本文毫无关系,不能因为否定《山海经》就连带把它们也斥为“奇异而迷离不明”。
《山海经•海内东经》的篇未,附有一段千字篇幅的文字,叙述二十余条水道的出处,流向和归宿,沅水和郁水就包括在其中。这段文字无论从体例和内容看都与经文本身无关。清人毕沅说:“右《海内东经》旧本合‘泯三江,首......’以下云云为篇,非,今附在后。”已指出两者之区别,为方便起见,下文简称该段文字为《海内东经》之附篇。附篇除了一句话以外,毫无离奇荒诞的内容,显而易见是一份极可宝贵和水道地理资料,其中或有个别文字错论,或有些地名无考,但所叙述的基本事实都与《汉志》、《水经》所载没有冲突,可资信赖。
其沅水条曰:“沅水出象郡镡城西,〔入〕东注江,入下隽西,合洞庭中。”比较之:《汉志》牂柯且兰本注云:“沅水东〔南〕北至益阳入江。”《说文》:“沅水出牂柯故且兰,东北入江。”
《水经》:“沅水出牂柯且兰县为旁沟水,又东至镡城县为沅水,又东北过临沅县南,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。”
沅水今古同名,以上四条记载,关于沅水的出处,流向和归宿大体一致,没有出入。但《海内东经》附篇的沅水条要早于其他三条史料,大致体现了秦汉之间的地理现实,时镡城以西之且兰地尚未内属,因此叙沅水源头只及“镡城西”。汉武帝以西之且地置为故且兰县改称且兰县,《水经》故言沅水出牂柯且兰,由地名的演变可以看出地理现实的变化。
附篇沅水条记事之准确,说明镡城曾属象郡这一史实是可信的。镡城于《汉志》为武陵郡属县,是武帝元鼎六年以后的事(这点后文还要详及),于秦代它正是象郡的北界。《淮南子•人间训》说秦始皇“又利越之犀角、象齿、翡翠、珠玑,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,一军塞镡城之岭......”,证明镡城正在秦、越之交界。秦始皇三十三年置象郡以后,镡城即成为象郡最北部的一县。《淮南子》此文亦为鄂氏所征引,但未能直接证明象郡日南说,反倒可以成为《海内东经》附篇沅水条的注脚。
《海内东经》附篇郁水条曰:“郁水出象郡,而西南注南海,入须陵东南。” 《汉志》郁林郡广郁县:“郁水首受夜郎豚水,东至四会入海。”
《水经》:“温水出牂柯夜郎县,又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,又东至领方县东,与斤南水合,东北入于郁。”
郁水即今西江及其上游红水河之古称。郁水之源,秦汉间尚不清楚,只知其出象郡,未能言其具体出山。《山海东经》附篇所叙二十六条水道不言详细出处者唯郁水与白水两条。白水今嘉陵江及其上游白龙江,源出蜀郡徼外,故亦仅能言其出蜀,不能详其出山,至武帝开西南夷,汉人地理知识更加扩大,知郁水(红水河)上源为豚水,豚水出牂柯夜郎,即今北盘江。但红水河另有一上源南盘江。于《汉志》称南盘江下游为温水,汉人视之为郁水支流。《汉志》牂柯郡镡封县本注曰:“温水东至广郁入郁。”合上文所引郁林郡广郁县本注观之,知温水与豚水合流后始称郁水,文郁县(今广西凌云、田林、凤山一带即在两不合流处,正是豚水、温水、郁水三名称的分界点。
到了写作《水经》的时代(近人定为三国时期)又移温水名于豚水之上,豚水名遂隐,故《水经》云:“温水出牂柯夜郎县,又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”,实际上相当于合《汉志》牂柯郡夜郎县:“豚水东至广郁”及郁林郡广郁县:“郁水首受夜郎豚水”两条注文为一。
郁水的流向是东偏南,《海内东经》言其“西南注南海”,西南应是东南之论。古籍经过长期辗转抄写,常有错讹,尤其是道里方向,东误为西,南讹为北的现象颇为常见。即如前引《汉志》云:“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”,东南显系东北之误,读史者决不至于因志文曰东南,而误认其为他水,同理,此处亦不会因经文言“西志注南海”而疑其非郁水。
郁水入海处于《汉志》为四会,于《海内东经》附篇为须陵。须陵划汉以前之地名,其地望今已无可指实,或许与四会是名异而实同。《水经》粗看似未言郁水之归宿,反言郁水与斤南水会合之后,又复入于郁,显然不通。因此《水经》温水条最后一名“东北入于郁”明白是“东南入于海”之论。入海误为入郁,东南讹为东北,必须如此更正于事理方合,也才与《水经》叙水道必详其出处、流程及归宿三要素的原则相符。
要之,《汉志》、《水经》与《海内东经》附篇有关郁水的记载表面上看来似乎有些差异,但实质完全一样,证明附篇郁水条所叙内容绝非虚妄。事实上,不但是上述沅、郁二水如此,《海内东经》附篇所有二十六条水道的纪录,者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地理资料。不能仅仅因为它附在《山海经》一书之内而忽视其地理价值。就这些水道资料所表达的地理知识来看,似乎写定于秦汉间,如言白水出得不系广汉而系于蜀,言沅水、郁水出处只及象郡,而不及其西;又全篇不及汉以后出现的新地名;叙水道归宿时先言入江或入某海,再及归宿处之地名,体例似比《汉志》、《水经》原始。唯全面之论证,已非本文所当及,容另文述之。
鄂卢梭氏以郁水当今右江--郁江--西江一系,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二册亦作如是观,显然与《汉志》所载不合。《汉志》以为郁水之上源是出自牂柯夜郎的豚水。夜郎今虽不能确指何地,要在贵州安顺以西南一带殆无异义,则豚水当今右江--西江,则夜郎只能位于今右江之源的滇桂之界一带。显然要与《史记•西南夷传》所载完全不合。《史记》说蜀枸酱是由夜郎经牂柯江到番禺。若夜郎在今右江之源,则枸酱运输路线将要越过南盘江与右江之分水岭再下右江,焉有是理?何不直走北盘江--红水河来得合理?汉人对豚水--郁水(北盘江--红水河--西江)一系本非常熟悉,又称之为牂柯江,是西南夷地区通岭南之交通要道。《汉志》关于豚水一郁水的记载也委清楚。因此,将右江--西江当成郁水是不妥的。
再说《茂陵书》。《茂陵书》或称《茂陵中书》。《汉书.王莽传》载:更始三年,赤眉亦军入长安:“宗庙园陵皆发掘,唯霸陵、杜陵完”。论者以为《茂陵中书》即于此时由武帝茂陵中发掘所得。是书久已亡佚,由臣瓒注《汉书》所引有关地理和制度诸条文看,或为武帝时人所作,其记载亦足当作信史。
鄂氏认为《茂陵书》“象郡治临尘,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”之文有脱误,这是正确的。因为同书载珠崖郡治瞫都,去长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,而儋耳去长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,临尘(今广西崇左)离此两县(在今海南岛)当然不致有万里之遥,因此里距应当有误。但鄂氏看法却相反,以为数字不易错,地名容易错。临尘可能是临邑之误,而临邑即林邑,进一步,林邑又是象林县,因此结论是:”象郡治象林县。但地名这样连环错法恐怕不可能,而且即使真是这般错法,要解释日南即象郡也还有困难:因为鄂氏自已已证明秦象郡和汉日南郡同治西捲县。现在若依照经他修正的《茂陵书》又说治象林,这就还要证明秦象郡曾由象林迁至西捲,对这一点,鄂氏也承认说不过去,“有些武断”。退一步说,如果象郡真治象林(今越南广南省会安附近),去长安亦远不足万七千五百里之数。数字讹误的可能性并不比地名小。本文其他章节所引用的《茂陵书》条文、地名均无疑问,但数字却间或不可信,如“沈黎治莋都......领二十一县”,领县数就明显有误。因此马氏所引《茂陵书》此条错的实在是里距,至于“象郡治临尘”的记载是完全可靠的。
再说《汉书·昭帝本纪》。鄂氏以为《昭纪》无凤五年“罢象郡,分属郁林、牂柯”之载,毫无根据,应毅然摒除。他引清人齐召南《汉书考证》说:“按此文可疑,秦置象郡,后属南越,汉破南越,即故象郡置日南郡,以《地理志》证之,此时无象郡名,且日南郡固始终未罢也。”齐氏此数语实不合逻辑,他并不是以其他材料来求证《昭纪》,如果这种考证成立,何不可以倒过来,以《昭纪》为可信来否定《地理志》注文?所以鄂氏也不得不承认此种考证“不甚详明”。同一齐召南,在遇到河西四郡置年地志和本纪所载有歧异时,不加深考,主张从本纪,因为本纪直采官家记注,最为可据;然而在象郡问题上却又一反从纪之主张,奉地志注文为圭臬,这一正一反适足明其考证之草率,并非择善而从,而是择易而从。
就一般情况而言,《史》、《汉》本纪的记载的确是比较可信的,在没有坚实旁证的情况下是不好随便摒弃的,而且就《昭纪》此文而言,确是可靠的。因为罢象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。在武帝几十年开疆拓土消耗了大量物力、财力后,昭帝年间明显地采取紧缩政策,罢省一系列边郡。始元五年,罢真番、临屯,以并乐浪,又罢儋耳并珠崖。元凤五年罢象郡的性质与上述三郡之罢完全一样,乃是以精简政区的方式来差减轻负担。因此,借用数学术语来说,昭帝罢象郡是一个“可能事件”,不可视为乌有。
武帝间象郡之存在还可从“十七初郡”中得到旁证。《史记.平准书》曰:“汉连兵三岁,诛羌,灭南越,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,且以其故俗治,毋赋税。”十七初郡之名目,《史记》未详。集解引晋灼曰:“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珠崖、儋耳郡;定西南夷,以为武都,牂柯、越嶲、沈黎、汶山郡;及《地理志》、《西南夷传》所置犍为、零陵、益州郡,凡十七也。”鄂卢氏因晋灼所说十七郡中,有一郡应该排除。零陵郡乃武帝分桂阳郡所置,绝非新开地上的初郡。除去零陵以后,此一空缺则非象郡莫属(后文还举一条旁证)。故鄂氏所举此条,适足以成其反证而已。
从《汉志》郁林郡领域相对较大这一点,亦使人相信象郡地分属郁林之可能。汉末岭南七郡规模较小,领县数不多。独郁林郡属县十二,这诸郡之冠,比南海、合浦、九真、日南等郡属县数多出一倍左右。推测其于武帝初置时,领域必无有如许之广,乃因后来接受象郡地后,才扩展至十二县之众。
以上已经从个别方面,独立地论证了马伯乐氏所举《海内东经》附篇、《茂陵书》、《昭帝纪》的四条记载,是可靠的史料。而更重要的是,通过这些史料的相互印证,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们的可信程度。《昭纪》云:“罢象郡,分属郁林、牂柯。”《茂陵书》则曰:“象郡治临尘”,临尘于《汉志》正是郁林郡属县。《海内东经》附篇又曰:“郁水出象郡”,于《汉志》,郁水上游正在郁林郡之中,证明郁林郡部分地确故属象郡所有。又曰:“沅水出象郡镡城西”,则更明确了秦象郡的北界。镡城于《汉志》属武陵郡,其南则郁林,其西南则牂柯,是证象郡应跨于郁林牂柯间。三种时代相去不远的不同载籍,从四个不同的角度,正好互为补充,综合说明了象郡问题的真相,这岂是偶然的巧合?当然不是。这只能说明《汉书•昭纪》关于象郡的纪载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,鄂氏对马氏所用史料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。
四、郁林说可解释象郡沿革而日南说不能
《昭纪》之可靠既已证实,若以之为基础,再补充若干史料,则象郡和岭南地区的沿革大略已明。
《史记•南越传》云:“秦已破灭,佗即南并桂林、象郡”,“岁余,离后崩,即罢兵。佗因此以兵威边,财物赂遗闽越、西瓯、骆,役属焉,东西万余里。” 《南越传•索隐》引《广州记》曰:“交趾有骆田,仰潮水上下,人食其田,名为骆人,有骆王骆侯,诸县名为骆将,铜印青绶,即今之令长也。后蜀王子将兵讨络侯,自称为安阳王,治封溪县,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,令二使典主交趾、九真二郡人。”
《水经•叶榆水注》所引《交州外域记》云:“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,土地有骆田......。”与《广州记》略同。
由此可知,岭南地区的沿革大略是:
秦始皇略定扬越,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。象郡南界与《汉志》郁林郡一致。象郡以现之交趾地(今红河三角洲一带)为蜀王子安阳国所在。秦亡后,南海尉越佗据南海自立,随之击并桂林、象郡。吕后文帝时,赵佗南越国之势鼎盛,以兵威边,灭象郡以南之安阳国,置交趾、九真二郡,形成地东西万里的大局面。武帝元鼎六年,平南越,置十郡(十郡之说后文另有证)。象郡建制保留至昭帝元凤间方罢。
这一沿革过程与上引史料毫无冲突,既简单明了,又顺理章,是证郁林说之可行。
若以日南说代之,则情况完全两样。鄂氏不得不对上述史料随意加以改造,添上许多假定和臆想,即便如此也还不能自圆其说。
首先他想象蜀王子所攻取的不是“未有郡县之时”的交趾,而是秦之象郡(直接与《交州外域记》矛盾)。然以秦之强大,何能为蜀王子所败?于是又必须进一步假定蜀王子之取象郡乃在秦始皇死后,但也不能太晚,太晚则与“秦已破灭,佗即击并桂林、象郡”之记载相刺缪。于是乎蜀王子不早不晚,只能在秦始皇死的那一年夺取象郡,而他所建立的安阳国也只能存在三年,到秦亡之时,即这赵佗击并。这哪里是在解释历史,完全是在随意编造了,然而,即使是这样编造,也并不圆满。秦始皇死后,天下虽已开始动乱,但中央集权制并未崩坏,终秦之世无有叛郡,便是明证。赵佗虽占据岭南地区的中心南海郡,其击并桂林、象郡犹须待秦亡以后,以小小蜀王子何能恰好于秦始皇一死就夺取偌大一个象郡?若象郡真成安阳国地,则《史记》必言佗击并桂林,灭安阳国,无有直书佗“击并桂林象郡”之理。而县安阳国若仅存三年,其事迹绝不可能成为传说而流传至数百年后。
《广州记》和《交州外域记》是根据掺有若干史实的传说写成的。因此安阳国的具体存在时间,也根本不可能象鄂氏所推测的那样绝对。从《史记》所载看来,赵佗灭安阳国当在吕后文帝间,即上引所谓“高后崩......因此以兵威边,财物骆遗闽越、西瓯、骆,役属焉”之时。但鄂氏既已认定佗并安阳国在秦亡时,则《史记》此文遂不可通。于是他又假设,此文乃是“追记之文”。
凡此种种莫须有的假设和臆想,皆由于死抱“日南郡即故秦象郡”之《汉志》注文不放的缘故。若相信《昭纪》的记载,主张象郡郁林说,则安阳国自在象郡以南交趾地,于秦汉间尚与赵佗无任何关系,殆至吕后以后方为赵佗所灭,置为交趾、九真两郡。这样解释圆通无碍,无须任何假设、臆想之辞,又与史籍所载相符,其合理性不是十分显著吗?
上文已经说过,《汉志》中有关郡国沿革的注文毛病不少,不可迷信;日南郡“即故秦象郡”更是一条孤证,它与《昭纪》的可靠记载相矛盾,已令人觉得其不可信,而鄂氏以之为据来说明象郡沿革又破绽百出,不能自圆其说。有了这样几重理由,日南即象郡之注文难道还不应该抛弃,这比鄂氏毫无道理地“毅然摒除”《昭纪》条文慎重多了。
班固对于秦郡并不尽了然。近人已证明秦一代郡数在四十以上,但依班固的看法,秦郡仅有三十六,一些他视为高帝所置的郡其实乃是秦郡。大约他以为秦郡与汉郡之间是一一对应的接续关系,秦桂林郡既被当成汉郁林郡的前身,秦象郡的后身当然要另找他郡,或许正因汉日南郡有象林县,遂被班固误认其与象郡有关,而被派作象郡的后身。
班固的真正思路是否如此,今已不明,这里不过略作推测而已。但他以为日南即象郡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,已为上文的论述所证实.不过象郡日南说的支持者还有两点不太充分的理由需要予驳正,一是北向户,一是西呕君。
五、关于北向户和西呕君
北向户向来不成其为问题,但长期来被纠缠不清,以为可当成日南说的证据,故需略缀数语。在北回归线上,每年夏至那一天正午,太阳正好位于天顶,此时,在回归线以南的地方看太阳,其位置自然在天顶偏北处,而且越往南走,太阳越偏北,光线也就可以从北向窗子射入室内,这就是北向户的意义。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带不能见到,因此人们将它作为南疆的一种特殊标志,以“南至北向户”表示秦帝国南疆的遥远。由于只要过了北回归线就会出现这种北向户现象,所以“南至北向户”一语只有定性的意义,并不能作为定量的标准。也就是说,只能表明秦代南境至少已到北回归线以南,而不能具体说明南至何处。当然,越往南走,太阳在天顶以北的日子越多,到了今越南中部的日南郡,北向户现象更加明显,但更加明显已是充分条件,而不是必要条件,也就是说,到了日南郡一定有北向户现象,但不能说,只有到了日南郡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合浦全郡、南海、苍梧、郁林南部都可以是北向户所在。因此鄂氏以此证明秦代南境已到达日南郡是没有说服力的。
而且即使在日南郡,出现北向户现象的日子也只在夏至前后的一段时间,其他大部分时候仍是南向视日。所以东汉日南张重举计入洛,明帝问他日南郡是否北向视日时,他并不以这然,并举例说云中、金城之名亦不必皆有其实。完全的北向户只有在南半球才能实现。我们显然不会因日南之名而以为其位于赤道以南,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“北向户”就非至日南郡不可。
西呕君译吁宋问题。《淮南子.人间训》载秦始皇发卒五十万与越人战,杀“西呕君吁宋”。西呕究在何处?有人认为西呕当即后来《汉志》交趾郡之西于县。呕、于两音同部,可以通转。因而以此证明秦军已深入到交趾地,否定象郡分属郁林、牂柯之说。以为西于县之名与西呕有关,本可备一说,未可厚非,但以之证明秦军杀西呕君译吁宋必在交趾地,却未必得当。有许多史料证明西瓯(即西呕)在桂林境内。如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七一引《郡国志》曰:“郁林为西瓯。”《史记•南越传》云:“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雒四十余万口降。”瓯雒即同传前述之西瓯、雒两族,至于唐以下载籍以西瓯地当秦之桂林者相当多,因非直接证据,无需具引。亦有人由考古方面来证实这一点。因此,西瓯族很有可能由交趾地转移到桂林地,而在交趾地遣留下西于这一地名。在地名学上,民族虽然已经迁徙,但他们留下的地名仍然存而不废,是屡见不鲜的事。徐中舒先生推测:“西于王为安阳王驱遂以后,乃北徙于桂林瓯雒地”,于事理颇合。故秦军杀西呕君译吁宋完全可能在桂林地,不必非在交趾地不可。这件事并不能作为秦象郡即汉日南郡的证据。
综上所说,象郡日南说的论据均已被否定,按理说来,应该可以无条件接受郁林说了,但是暂时还不行,还有最后一道难关,即所谓九郡问题需要克服。
六、武帝平南越实置十郡而非九郡
《史记•南越传》云:“......南越已平矣,遂为九郡。”九郡之名,《史记》不详。《汉书.武帝纪》作:“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珠崖、儋耳。”《南越传》与此同,唯将儋耳、珠崖列于最前面。然据《昭纪》,象郡应至元凤五年才罢,何以九郡之中无象郡之名?对这个问题有过两种回答。马伯乐氏认为,象郡或在武帝建无六年开西南夷时先归属于汉,待元鼎六年平南越置九郡时,自然不在其中。日本学者杉木直治郎则以为,九郡之名并不如《汉书.武纪》所列。因为《贾捐之传》、《地理志》篇末皆云儋耳、珠崖两郡为元封元年置,因此武帝元鼎六年之九郡,应是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七郡及桂林、象郡两郡。杜佑《通典》实际上已提出这个见解,其《州郡典•古南越地》注曰:“分秦之南海、桂林、象郡,置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日南、九真、交趾、并旧,九郡是。”
但是马氏之说,于史无征,没有说服力。杉木氏之设想亦无实据,未可从。且九郡之中若真有桂林,则该郡废于何时,又成另一悬案。杜佑《州郡典》之注文,亦纯属臆想而已。
要之,九郡问题的确比较棘手,历来成为证明汉代不存在象郡之铁证。凡主张象郡日南说者,包括鄂氏在内,无不以九郡之中无象郡之名作为否定《昭纪》的最强证据,其实这个证据完全是可以推翻的。
首先要肯定的是,汉武帝平南越后,所置实为十郡,而不是九郡,除《汉书.南越传》所载九郡以外,还应有象郡。元鼎六年所置者为大陆上的八郡,第二年,元封元年又渡海,在海南岛再置二郡。然则何以《史记》云“遂为九郡”呢?这自然有其原因。
平南越地,置十郡后,仅隔四年,元封五年间,武帝就在开疆拓土版图扩大一倍的情况下,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,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监察区,以便于行政管理,加强中央集权制。其中除象郡以外的故越地九郡被划在交趾史部之中。自元封五年至征和二年(《史记》大约完成于此时)的十几年间,太史公习闻交趾九郡之说,而交趾又是故越地,因此越地九郡的错觉就逐步形成而至牢不可拔。这种错觉的形成很自然,而且亦非仅此一例。高帝末年十五郡亦为太史公所习闻,然细数十五郡时,却误数入东郡、颍川二郡而忘记其于上年已分别益予梁国和淮阳两国。
然则象郡列入那一刺史部呢?曰:益州刺史部。杨雄《益州箴》曰:“岩岩岷山,古曰梁州......义兵征暴,遂国于汉,拓开疆宇,恢梁之野,列为十二,光羡虞夏......。”所谓“恢梁之野,列为十二”者乃汉武帝扩大了《禹贡》梁州的范围,列郡十二,以成益州。十二郡之目。顾颉刚先生曾数其中十一,即巴、蜀、汉中、广汉、犍为、牂柯、武都、汶山、沈黎、益州,而后说:“尚有一郡不可知,或后来有所并省。”此一郡其实可知,乃象郡也。由于象郡隶属益州刺史部,遂不与故越地其他九郡相提并论,故交趾九郡在太史公的印象中极为深刻,越地九郡之说遂见于《史记•南越传》之中。至班固著《汉书》时,遂据《史记》九郡之说,按图索骥,以汉末岭南七郡,加上海南岛已废之二郡,成九郡之数。此后南越地九郡之概念遂至不可移易矣。
由此可见,九郡之说有其历史原因,并不能因此否定象郡存在于西汉的事实。要之,武帝时岭南地区实际上并存有十郡,只是由于象郡单独列于益州刺史部之中,因此十郡并提的时间至多不过只有四年,在人们的印象中极为淡漠,故十郡之说遂不流行于世,象郡之下落亦随之不明。近人虽有以《昭纪》罢象郡之说为可信者,终因无法解释九郡之中何以无象郡之名,而不能理直气壮。究其实,《平准书》所言十七初郡已隐含象郡于其中,只因晋灼误以零陵代替象郡,后人不加深考,即宗其说,遂使象郡不见天日。陈梦家先生对晋注零陵郡亦有怀疑,然又并退犍为,而进酒泉、张掖,乃以错易错,至谭其骧师始云晋注应退零陵而进象郡。今幸《益州箴》“列为十二”之文具在,足以证成其说。于是象郡之存在于昭帝之前,既有《昭纪》之明确记载,又合十七初郡之数,复列于益部十二郡之中,并与太史公九郡
之说不相冲突,则至此象郡建置之谜已得彻底解决,而象郡之领域亦可随之而明矣。
七、象郡之领域
由《昭纪》象郡分属郁林、牂柯,及《茂陵书》象郡治临尘之说,知汉象郡应有《汉志》郁林郡西半部及牂柯郡部分地。其南界和西界北段当和《汉志》郁林郡同,与合浦、交趾、牂柯三郡为邻;西界北段当包有《汉志》牂柯郡毋敛县在内,该县位于郁林郡广郁县以东北,是牂柯郡唯一可能原属象郡之地。象郡北界即毋县之北境,东界无确征,要当沿今广西大明山-都阳山一线。此线东西各向成一地理单元,以东为桂中岩溶丘陵与平原,适足以自成一郡,郁林郡治布山即位于其中(今桂平县);以西为桂西山地与郁江流域平原,即为象郡领域,象郡治临尘即在郁江支流左江岸边(今崇左县)。
马伯乐氏未指出秦汉象郡之区别,其实秦象郡之领域比汉象郡要大。北面应有《汉志》武陵郡镡城县,东南或有合浦郡之西部地,如图所示。
镡城属武陵乃武帝元鼎六年以后之事。武帝平南越后,即调整与故南越地相邻诸郡之南界:以故属秦南海郡之曲江、含0、浈阳、阳山四县地北属桂阳郡(四县地在阳山,横浦两关以南,两关原为南越与桂阳郡亦即秦南海与长沙郡之界);以故属秦桂林郡之始安县地北属零陵郡(始安地在灵渠以南,史禄通灵渠前不属秦所有),以故属秦象郡之镡城县北属武陵郡;复以故属汉桂阳郡之谢沐、冯乘县地南属苍梧郡(以上所列县名皆据《汉志》为说,除镡城县外,元鼎间未必均已出现)。合浦郡为武帝新置,该郡必分自故秦三郡,故推测其西部原属象郡,其东部或原属桂林。
_____________
(1)见其所著 La commandrie de Siang (《象郡》),冯承钧译:《秦汉象郡考》,载《西域南海史地译丛第四编》。
(2)La premiere conquete chionise des pays annamites(《中国对安南的最初统治》),冯承钧译:《秦代初平南越考》,载《西城南海史地译丛第九编》,本章对此文之引语皆据冯译本。
(3)《秦四十郡辨》潜研堂文集卷十六。
(4)《汉志》日南郡补注。
(5)严耕望《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》,载“中央研究院院刊”第一辑(1954年)(台湾)。
(6)《后汉书.南蛮传》。
(7)参见周振鹤《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》有关章节,载本刊1982年第三、四辑。
(8)《山海经古今篇目考》,《经训堂丛书》所收。
(9)于《汉志》白水系广汉郡甸氏道下,注曰:‘白水出徼外......“,广汉高帝置,秦为蜀郡地。
(10)不过汉人似亦未穷豚水之源,至三国时期方知豚水之上源存水(今北盘江上源革香河)。
(11) 南盘江上游《汉志》另以桥水当之,这里已无法详述。
(12) 此处温水尚可有其他两种解释:1.“温”为“豚”之误;2.温水与《汉志》温水同,指南盘江,但南盘江源不在夜郎,此一说有困难。
(13) 戴震区别《水经注》经注文的原则为:“......凡一水之名,经则首句标明,后不重举,注则文多旁涉,必重举其名以更端。”依此原则郁水前已见,后文亦不当有复入于郁之语。
(14) 陈澧《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》即持此观点。
(15) 姚振宗《汉书艺文志拾补》有此说。
(16) 参见前引周文第十章。
(17) 主张象郡日南说者,皆以为象郡北界必在汉交趾郡以北,并非认为象郡完全等于日南郡,否则象郡领域毋乃太小,而且与桂林郡不相连。因此蜀王子所取只能假设为象郡,而不是未有郡县之交趾。若承认蜀王子所取为未有郡县时之交趾,等于承认象郡未至交趾地,日南说将不攻自破。
(18) 见《温水注》所引范泰《古今善言》。
(19) 蒋廷瑜:《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》,载《百越民族史论文集》。
(20) 《交州外域记》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,载《论巴蜀文化》一书。
(21) 见《秦汉两代における中国南境の问题》,载《史学杂志》59编11号(1950年)。
(22) 顾颉刚、谭其骧:《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》,载《复旦学报》1980年第3期。
(23) 见其《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》,载《汉简缀述》一书,并参见前引周文第三章。
(24) 《历史大辞典》条目之一:“十七初郡”,见《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》1980年第9-10期。
(25) 参见前引文第十章并长沙马王堆出土古地图。
原载于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4年第3辑,又见于作者文集《学腊一十九》(山东教育出版社,1999年)第29-54页。注释请对照原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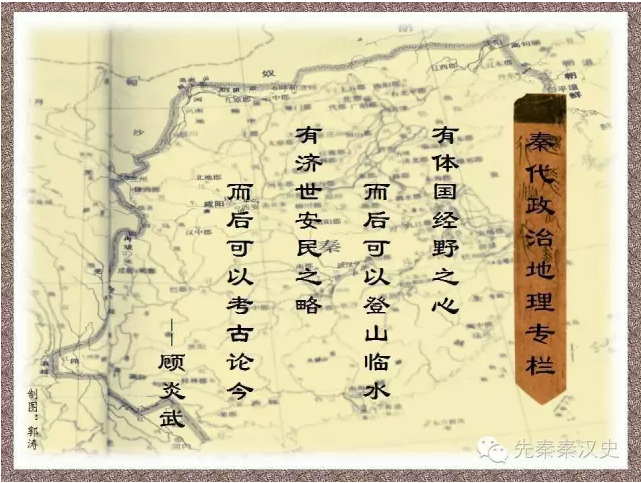
 评论
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