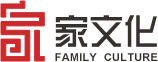“十陕九不通,一通便成龙”。大潮所至,风云际会,陕人近现代通而成龙者不知凡几,于右任和井勿幕,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中国论文网 http://www.xzbu.com/5/view-1516613.htm
于右任,光绪五年(1879)生人,三原籍,贫家孤儿,举人出身。庚子岁两宫西狩,上书陕抚岑春煊,“请其手刃西后,重新行政”;甲辰年(1904)以《半哭半笑楼诗草》被清廷通缉,亡命宁沪。创办《神州日报》及《民立》《民呼》《民吁》诸报,创建上海大学、西安中山学院、西北农林专科学校、渭北中学、民治中学诸校,曾经亲炙中山先生謦�,以文人而衔命统帅护法靖国军于陕西,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次长,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、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、监察院院长等职,年德资望,为国共两党诸多高层政要所推戴,以爱国诗人、近代草圣彪炳史册,1964年以八十六岁高龄病逝于宝岛台湾,多誉多寿。
井勿幕,光绪十四年(1888)生人,蒲城籍,巨室之后,任侠好剑。父丧家败后,十三岁即以避债游学四川,十五岁又以数金冒险随熊克武等蜀中志士负笈东瀛,向章太炎先生问学,得孙文、黄兴器重,几度回陕播撒革命火种,发动聚积革命力量,为同盟会陕西支部缔造者,辛亥武昌首义,西安得率先响应,实居首功,孙、黄对其有“西北革命巨柱”之许,豪迈多才,能文能武,而志行高洁尤为秦中时人后人所尊崇,1918年11月以不足三十一岁英年意外遇刺于陕西兴平,惨无晚年。
蒲、原毗邻,两人是连畔种地的乡党,但缘于各自的经历,1906年在日本始相交结,1915年底共同与康宝忠、张季鸾在上海密谋反袁称帝,1917年夏又一起与张钫、李根源等,在陕西酝酿起兵反抗北洋军阀。1918年于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,同年秋井被推陕西靖国军总指挥,不算以前的交往,其真正的合作共事的时间,仅短短的个把月,而就这个把月及这个把月所发生的一切,却足以让于右任肝肠寸断,铭记终生。
祸起萧墙
辛亥推翻帝制与满清统治之后,陕西也与全国同其大势,各种新旧力量纠结沉浮,国民党内部亦遽生裂变。民国临时政府成立,井勿幕因事功昭著被任为中央稽勋局副局长,却以陕事牵掣,辞未赴任;中山先生畀大总统于袁世凯后,井勿幕功成不居,亦遣散其部曲,仅留部分军队屯垦于陕北黄龙山一带,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,参众两院议员选出不久,便以革命告成不屑苟容而出关南游。中山先生发动“二次革命,井勿幕约刘守中赴汉口和曹印侯共谋讨袁,事败后避居日本。及袁帝制自为,在上海与康宝忠张季鸾等密谋起事不成,旋和熊克武经越南赴云南参加护国战争,奔走于蔡锷和熊克武军之间。在此之前,袁世凯派陆建章督陕。陆长北京执法处时,广杀党人,有“屠户”之称,入陕后积极附袁,婪杀自固,并命其子陆承武亲率“中坚团”驻防渭北,然而富平一役,即被陕军胡景翼等打得大败,承武被擒,西安被围,甘肃、山西在陕的刘冠三、邓宝珊、续西峰等,也竞谋起兵以讨之,一时四面楚歌。陆建章恐惧无计,打算让出西安以赎承武。在此关头,陈树藩尽率所部陕军由大荔、蒲城两地驰至三原,假“陕西护国军”名义,以保护陆氏父子性命与财产为条件,迫其交出陕督一职。建章穷窘无奈,遂电袁世凯“力荐”树藩以代己,俾便从容离陕,树藩得借机入主西安,攫取省政。想不到督陕之后,陈竟一变反袁为附袁,袁死之后,甚至通电谬推袁为“中华不祧之祖,万世共戴之尊”,顿致陕西同志汹汹大愤,纷纷相继离去。而树藩执迷不悟,又与皖系段祺瑞私扯师生之谊,袁死转而依附于段,欲借北洋势力以压迫陕西民军。“陕政日苛,陕难未已”,当时川、陕同志率多建议勿幕回陕以制之,勿幕亦慨然自往不辞,唯因此前京、沪同志响应黎元洪“军民分治”之议,已活动让滇粤桂军都参谋李根源出任陕西省长,以牵制树藩,勿幕回陕时李已到职,于是便应李氏之力邀,屈就关中道尹一职,借以就近与陈周旋,暗中策划倒陈。
1917年,府院相争,段祺瑞唆使附己各省组织督军团,逼迫解散国会。陈树藩闻风响应,遽以武力逼迫省长李根源解职,交出印信,并派兵围守根源寓所达五个月之久,若非著名人士宋伯鲁、宋联奎等竭力营救,李几至死。勿幕愤而辞去道尹,但以不便脱身而困居西安。12月3日,陕军骑兵团团长高峻率先在白水宣布独立,并以“西北护法军总司令”名义,传檄渭河南北,“反段倒陈”;12月10日,陕军警备军统领耿直,不直树藩为人,“乃暗使其参谋范润生赴广州晋谒孙大元帅,详陈西北情形,请示机宜,得委为陕西招抚使,与郭坚密使往来,决计除陈。”闻陈欲裁汰警备军,借机在西安向陈树藩发难,退出后与前统领郭坚会和,仿西南诸省“靖国军”名号,打出“陕西靖国军”旗帜,联名通电“讨段倒陈”;次年1月25日,陕军胡景翼团补备营营长张义安与董振五、邓宝珊部在三原起义,胡景翼、曹世英旋亦分别率部自富平、耀县赶至,宣布成立“陕西靖国军”,以左右两翼总司令之名义,发布《讨陈檄文》;稍后陕军樊钟秀团、绥远骑兵卢占奎部,亦相继加入反对陈树藩的行列。
此其时也,靖国各军连连报捷,一度几乎迫近省垣,其中省西蒲阳村一役,张义安以少敌多,尤使树藩为之不安。但为时不久,河南刘镇华见陈以省长为饵相邀,奉北京政府之命入陕援陈,山西阎锡山部也蠢然出兵西扰,耿直、张义安先后阵亡,形势转趋严峻。勿幕见靖国军各路彼此互不统属,号令不一,消息不灵,联系不周,不能形成合力,频频贻误战机,遂秘密派人与三原同志商议,一方面鼓动公请年德颇孚众望的于右任由沪回陕,以一军心,下势扭转混乱涣散的局面;一方面与南方护法之师取得联系,互为犄角,以储备北方革命力量。同时,鉴于西南靖国军唐继尧部有援陕之意,熊克武已驱走刘存厚而自为川督,又秘密派人经熊向唐请派川、滇、黔各军叶荃、但懋辛、石青阳等部共出关中,驰援陕西。1918年8月8日,间关抵陕的于右任三原誓师,发表就职通电和布告,与张钫宣誓就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,宣布取消各自原有名号,统一整编各部,建总司令部于三原设总部于三原。同年9月,叶荃率滇军由甘入陕,先至凤翔;王安澜等部则由鄂西北尽拔安康、南郑各地,吕超则出川北向陕南进发,旌旗云合,羽檄交驰,靖国军声势复盛。西路各县除�县、兴平外,悉归靖国军范围。陈氏震恐,然却不知这一切皆勿幕幕后运作,由于此前胡景翼故市为其骗掳,时尚囚于西安,于是一面向北京政府求援,一面又因勿幕与胡谊同莫逆,卑辞泥请勿幕与彭仲翔以调人身份,至三原劝降胡景翼部以抵制叶荃滇军。井勿幕将计就计,却佯示不远离省,而愈是如此,陈则促之愈急,勿幕与彭遂趁机远�,智脱樊笼矣。一到三原,即为于右任所借重,公推井为总指挥,授予彭仲翔军务处处长,让井臂助其主持军事大计,并很快就决定集中兵力于兴平、��,肃清咸阳以西地区,以扭转三秦局势。张钫督率靖国军二路和一路一部分布防渭河以南,一、三、四、六路及叶荃滇军布防渭河以北,从岐山、扶风、武功、兴平到乾县、醴泉,连营数百里,井勿幕亲赴前线,英气勃发,协同规划一切,全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态势,孰料当井勿幕奉命率岳维峻、董振五等到凤翔视察驰劳各军,“是时贾福堂复叛靖国军,多为残暴行,自咸阳以西时人谓之‘黑暗地狱’。”勿幕返回途中,即集合第四第六两路兵环攻兴平,数日未下,第一路郭坚命新降李栋材营驻南仁堡策应。某日栋材以郭坚名义函约勿幕于驻地会议,因李、郭同籍蒲城,李亦“素来仰慕井氏兄弟”,且是与熟人、部属相见,勿幕不顾他人提醒和劝阻,慨然仅带数人前往。“及往,郭固未在,则见李栋材迎之入室,方寒暄间,忽有人报郭司令至矣,井出往迎,甫至门外,栋材遽自后发枪击井,井及从者皆死”。李并当下割取勿幕首级,星夜拔营渡渭,赴西安向陈树藩报功。时正坐镇陕北的勿幕之兄井岳秀闻之,亟向树藩催索凶手以报仇,树藩与井氏昆仲关系素近,既忌岳秀因此反目衔恨,于己不利,又恐两军对垒,前途未卜,未便杜绝邀功之门,筹思多日之后,遂将栋材“资遣”,俾之远离陕西,而将勿幕首级派人函送时持中立的泾阳田玉洁部,由田转交三原靖国军总部,以示此事与己无关。可怜勿幕,竟以身首分离,匆匆槁葬于蒲城东门之外,从而酿成轰动一时、影响深远的“井案”。
违心指凶
“井案”对陕西靖国军的打击是致命的。史载自此“诸军失其联系,成顿蹙之势。叶相石(即叶荃)以孤军走耀县,其余援军有观望者,有变方略者,自是至民国十一年止,四年之间靖国军以一隅之地,当七省之兵,受兵弥烈,虽经于右任以大义大节至严至正及大无畏之精神激励同志,抗拒敌人,已备尝播迁之苦矣”。然则如此惊天大案究是谁人制造的呢?世人皆知勿幕是为李栋材所杀,但是栋材与井份属同乡,熟稔而无宿怨,缺乏基本的作案动机 ,而其作为中隔数层一下级军官,倘无有力之人主持或主张,即欲杀井,亦谈何容易?所以舆论普遍认为其背后肯定另有主谋。至于是谁,则长期仁智不一,疑点主要集中在两三个人身上。
一个是郭坚。因为第一,人多风传郭坚部队纪律一向不好,勿幕对此曾有所“箴规”,“郭深衔之”;第二,勿幕去南仁堡是应郭坚信约;第三,李栋材曾为陈树藩亲信马弁,与郭坚亦相狎好,此时已然投至郭坚帐下;第四,除栋材外,参与刺杀勿幕的李新生、任申娃悉为郭坚手下,事后郭坚不仅未予追究,甚至竟让此二人都当了连长;第五,勿幕去南仁堡是郭坚所约,郭坚本人却没去;第六,勿幕去南仁堡前,曾致信熊克武说很多人都劝他勿去,恐有危险。
再一个是陈树藩。因为第一,陈虽与井有旧,但此前树藩“请”其去三原,意在借其声望收抚胡景翼部队,瓦解靖国军,没想到勿幕耍弄于他,不仅未按其意图行事,反倒担任了敌军的总指挥,直接和他对垒,使他既悔又恨;第二,李栋材戕杀勿幕时虽在郭坚麾下,但他曾是陈一亲信马弁和营长,杀了勿幕之后,又割下其首级径赴西安向陈报功,陈一开始还让他官复其原职;第三,井岳秀为了给乃弟报仇,屡次要陈交出凶手,陈不愿交,亦不敢留,资助栋材一笔巨款,让其远遁汉口租界以躲避。
还有一个是马凌甫。理由有三:一是辛亥之前,陕西旅日学生分为关陇(咸长)、夏声(渭北)两派,井隶夏声,马属关陇,政治观点不同,某次开会争吵,夏声派曾动手打马,马认定系勿幕指使,一直怀恨在心。二是勿幕任总指挥后,出以治军公心,对郭部纪律“有所箴规”,时任郭部参谋长的马氏囿于个人成见和小集团私利,认为其私心自用,故意找茬,遂起害井之心。三是上世纪四十年代,陕西党人咸议公葬勿幕,户县华孝康登报广征证人证言,提出郭坚约井之函,系“马凌甫以参谋长职权命令张�(蒲城人,为郭差弁,摹郭书法酷肖)以郭的名义缮发的”,并持张�给当年郭的亲信冯绍芳的来信以为佐证,控之于长安地方法院。
从目前研究的结果看,这三个嫌疑人中,马凌甫疑点最大,大至几乎可以肯定地说,此事就是他一手策划的,而郭坚和陈树藩则多少有冤枉。根据是,对陈树藩而言,虽然勿幕之死,他是最大最直接的得益者,但是勿幕离开西安之后,龙归大海,已非他所能控制。勿幕兴平遇阻,事出偶然,此事让李栋材赶上,尤属偶然,彼何从而预知其必去凤翔视察劳军?返经兴平,又必然会攻打贾福堂且必然会去南仁堡,从而与栋材合谋而杀之?两军对垒,李栋材刺杀勿幕后,兴平既不能待,则其渡河投奔西安而来,当是再自然不过之事,不能仅凭其杀井投陈,就怀疑陈是真凶。对郭坚而言,豪放不羁,史传与井向有隔阂,但张钫说先一日勿幕访他,并约郭坚一起晤谈,“郭坚曾对勿幕说,‘乡党中瞧不起我这小贼,请乡党照顾咱一点,让咱拼个样子你看’。勿幕当时很客气地说:‘往日的责备,正是爱之深,不觉言之切,以后开诚相见,有错改错,勿存意见,勿听闲话。’郭亦释然,看不出有何深仇大恨存在胸中。”不能因为勿幕治军严格,批评过郭部纪律不整,李栋材杀井时为郭的部下,郭没赴约,李新生、任申娃也未被追究并被提拔当了连长,就怀疑郭是主谋。何况,郭坚为人爽直,作为一路主帅将领,大敌当前,亲痛仇快的道理,他还不至不懂,这样做“未免代价太大”。然而马凌甫则不同。除过上述三条理由外,华孝康《井案纪实》记载郭坚马弁张�给他的函称:“井先生之死,老司令(指郭坚)竟蒙不白之冤。其实命我写信召集会议者,马参谋长也;带我等驻扎马嵬坡,亦马参谋(长也)。是日弟赴正西,新生等往右翼赴南仁村,催李栋材开兵,不料竟下此毒手!”及郭坚亲信冯绍芳给他的函称:“当勿幕死时,弟远在上海,及弟由上海返凤翔时,多方侦察,略知一二。虽由郭坚背负不美之名,杀人由李栋材操刀,但动机杀人者,大有人在。明显一点说,即今日省中委之一人也”。都排除郭坚而认准是马,而他自己对马亦追索峻急,尽管法院以追诉时效已过不予立案,马却因此不安于位辞却省府委员远赴他地,也说明了这一点。再说,景梅九《追悼亡友勿幕之诗心》:“昨闻师子敬谓陈伯生(即树藩)接到勿幕遇害消息,顿足垂泪,因知杀勿幕非伯生意也。然伯生率以是败,则拟以子胥临终抉目悬吴东门,视越军入吴之情,亦无不合”云云。熊克武《我与井勿幕的交往》:“事后,外界传闻(上海方面的同志曾通一等也说)井勿幕同志是被陕督陈树藩杀害的。可是后来陈树藩来到四川达县,住在旧川军的一位军官家中,那时我已卸职闲居成都,他好几次托人向我说他要来成都和我见面谈谈。并且又说,井勿幕同志之死,有些人总说是他主使杀害的,他愿发誓与他无关,这件事自然有人明白。他言下之意,显然是指井之死是我们(靖国军)内部人干出来的”云云,两人与勿幕堪称至交,亦均一致为陈树藩开脱,应该都是有力的证据。
然而,当时比谁都更关心“井案”内幕,也应该比谁都更了解“井案”内幕的于右任,则既不说是郭坚,也不说是郭坚身边之马凌甫,却一口咬定是陈树藩所为。他的著名的挽井勿幕联,就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这种态度:
我哭井勿幕,耿耿爱国热忱,不亚宋渔父;
谁言李栋材,明明杀人凶杷,就是陈树藩!
据今看来,这显然是他的违心之论,然而依当时的形势,他又不得不如此说法。因为:从舆论上讲,勿幕被刺,人情汹汹,众人一致要求追查凶手,作为总司令的于右任,不能不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待,而陈树藩正其选也。首先,陕西靖国军是“反段驱陈”的产物,没有陈树藩的行为乖张,就没有陕西靖国军;没有陕西靖国军,就没有陕西靖国军与陈树藩的对抗;而没有陕西靖国军与陈树藩的对抗,自然也就没有和不会有井勿幕的被害。这个道理,最容易被人接受。其次,李栋材原为陈树藩亲信部下,又是具体实施刺杀勿幕阴谋的凶手,杀井得手,陈是最大最直接的得益者,其携井首级急赴西安邀功,陈不仅不将其交出,反而复其原职,并进而重金“资遣”使之远逸,种种迹象似乎在说明他与“井案”脱不离手,说勿幕就是他所谋害,顺理成章。
从当时的形势讲,道理不言而喻,于右任是靖国军的总司令,他之回陕担任总司令,就是因为靖国军内部成分复杂,难于统一。现在全军“倚重之胡君 (即胡景翼)未及脱险,而英烈之井君又遭惨祸”,战事空前吃紧,团结更是当前第一要义。推心置腹,他实在不愿和不敢相信勿幕为内部奸人所害,而毋宁希望是陈树藩干的。退一步讲,即便是郭坚或郭坚身边的马凌甫谋杀了勿幕,形格势禁,他于右任又能如何?口诛笔伐,无异于自暴其丑;鸣鼓攻之,又不正是仇敌陈树藩所梦寐以求的吗?他不得不设法把部队捏合在一起,不得不为靖国军的内部团结(哪怕是表面的、暂时的)与前途考虑。为此,他必须说是陈树藩,也只能说是陈树藩。如此既可以避免因追究凶手而导致靖国军内部更加分裂,使得全军上下同仇敌忾,不给陈树藩以可乘之隙,也足以使内部设谋杀害井勿幕的人心中不安,为自己鲁莽灭裂、褊狭自私闯下的弥天大祸,深自愧悔。虽然这样难免与事实不符,冤枉了陈树藩。
于右任毕竟是于右任。大将殒命,群情激愤,传言的“陈树藩杀井”“郭坚杀井”和“马凌甫杀井”三种说法,他肯定做过比较分析而有所心得。他的毫不含糊地一口咬定陈树藩就是杀害井勿幕的元凶,实在是高明的一着,是大敌当前痛定思痛之后所做的最为明智的选择。“谁言李栋材,明明杀人凶犯,就是陈树藩”,明截、忿激和不容置辩的口气之外,还明白地蕴含着一份惊人的机智与太苦太苦的用心,不是吗?
痛悼绵思
“井案”对于右任的打击,也是创巨痛深的。他深知勿幕的为人和才干,也最清楚勿幕的价值所在。他的回陕主持靖国军,是井勿幕多方运动,派人迎请的;靖国军难得的一段短暂的辉煌,也是井勿幕计脱樊笼来到三原后,帮他实现的。回陕时他身衔中山先生使命,怀抱一腔热情,全体将士也是人人振奋,个个用命,然而曾几何时,变生肘腋,斯人远去,形势转又变成这般模样,其哀恸、苦闷的心情,可想而知。所以,其稍后《致广州参议院电》中,痛书:“噩耗传来,五内俱裂。凡我将士,莫不悲痛。我军倚重之胡君未及脱险,而英烈之井君又遭惨祸,天乎何心,坏我长城?右任扶躬自咎,愤恨何及!旋念逆氛未扫,陕难方深,际此危艰,责无旁贷,惟有誓灭国贼,慰我先烈诸公。”伤悲、自责与夫弘其遗志之情,透于纸背;其给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呈文,说:“陕西民军奄有一隅之地,独挡七省之兵,苦战经年,夷伤接踵,猿鹤虫沙,经沐玄黄之血,旗当中鼎,应铭将帅之勋”,盛称勿幕“名家龙虎,关中麟凤,奔走南北者十余年,经营蜀秦者可百余战。慨虎口之久居,已乌头之早白。淮阴入汉,旋登上将之坛;士会渡河,胥慰吾人之望。讵意武侯之指挥未定.君叔之志惧歼。于11月21日被刺于兴平之南仁堡。莫归先轸之元,空洒平陵之泪”,慨然以韩信、士会、诸葛亮、来歙等古名人以拟之,极尽推崇之词,“拟请照陆军中将阵亡例给恤”。并含悲忍泪而作《吊井勿幕》诗一首:
十日才归先轸元,英雄遗憾复何言
渡河有恨收群贼,殉国无名哭九原;
秋兴诗存难和韵,南仁村远莫招魂:
还期破敌收功日,特起邱山拟宋园。
对井的莫名之死深表遗憾,发愿革命成功之后,一定要为他建一座像沪上宋园那样的墓园以志纪念。第二年,靖国军诸事不顺,继母刘太夫人去世。于右任公私窘迫,心力交瘁之际,又作《家祭后出城有怀井勿幕》诗云:
云暗关门间道回,戎衣墨�鬓双摧;
何堪野祭还家祭,不独人哀亦自哀;
桴鼓经年空涕泪,河山四战一徘徊;
东征大业凭谁共? 唤得英灵去复来。
对井勿幕益发思念。甚至1921年获悉井岳秀于汉口捕得李栋材,押回榆林将其剥皮剜心致祭于勿幕灵前后,悲不自胜,还专门写了一首《题井勿幕小照》:
羞为榆塞剜心祭,忍读余杭志墓文;
何以报国双泪眼,哭声直使帝天闻!
兀自伤感不已,为勿幕被害而深自痛责。据已知的资料,这种情绪,于右任一直保持了很长时间。1933年,华孝康在西安觅得一册元代书法家赵孟�临写的《兰亭序》,赴京请其题写跋语,因此帖为井勿幕生前旧物,后面还有勿幕死后不久,同样也被靖国军内部人戕杀的于鹤九画的山水画,他睹物怀人,自忖“自陕西靖国军起后,张义安、董振五、井勿幕、于鹤九、李春堂诸同志先后殉难,而此册则井、于二公精灵寄焉”,于是又赋《题华孝康藏赵临兰亭序》一首,再寄其哀:
回思于井诸君子,正气支撑靖国军;
一册兰亭映残画,抚摩如哭故人坟。
见物如见坟头,这是何等的感情!显见伤痛依然不减当年,至今读之,犹有催人泪下之感。直到十多年后偶然忆及陕西靖国军及西安“围城”诸役,他还作了十首《中吕・醉高歌》。其中第六首曰:
【前调】魂招东里心惊,路入南仁月冷;山河百战人民病,五丈原头自省。
诗中第二句的“路入南仁月冷”,就是讲井勿幕和“井案”的。何为同志、战友?何为刻骨铭心?读过右任先生的这些诗文,大致便可找到真谛,知道所谓“人间真情”,并非全是虚语。
1945年,对国家民族来说,是个极重要的年份,对于右任和井勿幕,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。这一年日寇投降,浴血奋战达八年的中华民族终于取得胜利,而此前陕西党人一直争取对勿幕举行公葬的夙愿,也终于得以落实。1943年8月,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勿幕。1945年11月17日,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请国民政府追赠勿幕陆军上将,并准陕西各界所请,补助勿幕迁葬费一百万元,届时派于右任回陕主祭。勿幕逝世27周年纪念日,即1945年11月21日,公葬隆重举行,于右任亲临主祭并徒步送殡,安葬勿幕于西安南郊少陵原清凉寺墓园,并公开发表《祭井勿幕文》如下:
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,于右任谨以香花清酒致祭于井勿幕先生之位。文曰:公之成仁,二十七载,雪涕追怀,泪痕犹在。维公生平,雄才大略,以身许国,率师东渡,爰定同蒲,乃克解潞。滇池起兵,翊赞松坡,义旗北指,胆慑群魔。靖国肇造,公羁省城,假名说降,突脱樊笼。同肩巨任,共擘戎机,六军将士,由公指挥。出师西征,我送其行,慎防奸宄,反复叮咛,公曰毋念,敌已有间。招之来归,若操左券,讵中奸计,殉国南仁,我军不振,此其大因。呜呼,廿余年中,国事蜩螳,今逢胜利,授令褒扬。终南之麓,曲江之旁,英灵永寄,云水苍茫。尚�。
深情历述勿幕的优长和辛亥以来的杰出贡献,说到勿幕对他的鼎力襄助和他对勿幕悠长的思念,也含蓄但却不失明白地表达了他对“井案”主谋的看法。至此,事情终于才算画上了句号,而他,也才终于兑现了对勿幕的承诺,从而释然坦然,给人感觉比早先轻松了许多。
这里值得一提的是,于右任这些悼念勿幕的诗联中,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,即宋教仁。宋教仁,近代民主革命家,字�初,号渔夫,湖南桃源人。曾参与发起华兴会和同盟会,为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,民初曾任法制院总裁、农林总长等职,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后,代理理事长,国民党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后,亟思成立政党内阁,为袁世凯所忌。1913年3月20日晚回湘探亲后经上海去北京,行前去《民立报》馆与诸友话别,于右任等送至上海北站时,被袁世凯亲信赵秉钧派人刺杀。于等急送宋教仁去沪宁铁路医院抢救,终因伤重不治,以三十一岁身亡,导致耸动全国之“宋案”。于联吊井勿幕联上句“不亚宋渔父”的“宋渔父”,指的是他,于诗《吊井勿幕》末句“特起邱山拟宋园”的“宋园”,指的是他的墓园,看得出在于右任的眼中,井勿幕是可以和这位中国宪政先驱相提并论的。何以如此?井、宋二人都是他的亲密战友,其遇刺都和自己有关,有就近取譬之便,而联中说井“耿耿爱国热情,不亚宋渔父”,也是个重要的原因,但是更重要的,当是与他们二人有许多相近或相似之处有关。如与宋教仁一样,勿幕也是一位辛亥革命先驱,虽然总体上讲宋更长于政论、宣传,井则宣传之外,更重于实际发动,然其运动辛亥革命之事功,亦足以向前者一样彪炳青史。如与宋教仁一样,勿幕也是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积极反对者,宋力倡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,到处发表演讲,反对袁世凯的专权,井则袁甫称帝,即径赴云南参与蔡锷发动的护国之役,与之以武力相抗;袁取消号帝之后,复联合民党人士发表宣言,力阻其再称总统,其民主革命精神,与前者要无二致。而“井案”和曾经轰动全国的“宋案”,更有如下两点惊人相似的地方:
其一,与宋一样,井勿幕也是为民主革命而光荣捐躯者,宋死时31岁,案惊天下,井殁时亦三十一岁,同样举世瞩目。两人均为不世之才,而同样英年早逝,识者殊觉惋惜,是当时议论较多之话题。
其二,与宋一样,井勿幕也是遭人暗杀的:一个时为1913年3月20日,一个时为1918年11月21日;一个过两天毙命,一个当即身亡。而刺宋的,谁都知道是袁世凯,杀井的,则不用说是自己阵营内的“奸人”,但是形格势禁,宋死之时,谁都不好说出真相。如于右任在宋遇害周年为宋所撰碑词说:
先生之死,天下惜之;先生之行,天下知之,吾又何记!
为直笔乎?直笔人戮!为曲笔乎,曲笔天诛!呜呼,九泉之泪,天下之血,老友之笔,贼人之铁!勒之空山,期之良史,铭诸心肝,质诸天地。
意即大家心里都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,但是格于形势,谁都不能说,不敢说――直说了恐有性命之虞,曲说了又怕招致天谴,只好“勒之空山,期之良史,铭诸心肝,质诸天地”了。勿幕之死也一样,虽然于右任清楚地知道凶手就是自己的手下,但是为了靖国军内部的团结,为了不影响广大将士对敌斗争的情绪,为了当时他所倾心的革命大业不致中途夭折,即使再委屈和再愤懑,也只能私下捏了鼻子,隐忍不便直说,所以一想到井勿幕和“井案”,便不由得将其事和当年的宋教仁和“宋案”联系起来,一以表彰勿幕先生的革命事功,一以表达自己痛楚而难为外人言道的心情。吊井勿幕联是这样,《吊井勿幕》诗是这样,就是《题井勿幕小照》的“羞为榆塞剜心祭,忍读余杭志墓文”、《题华孝康藏赵临兰亭序》的“ 一册兰亭映残画,抚摩如哭故人坟”,和《中吕・醉高歌》的“路入南仁月冷”,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宋教仁的“宋案”,也同样都包含着这样的委曲和委屈,都能读出苦不堪言,愧对故人的歉疚况味。说勿幕之死曾为右任先生的一大心结,这话当不为无谱。
 评论
评论